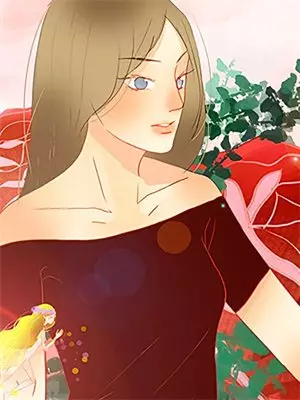
重生后第一眼,我看见妻子养在外面的男人。上辈子我忍了他五年,假装不知道这段奸情。
可这一次,他在雨里抬头看我的瞬间——我突然明白前妻为什么出轨了。这辈子,
我决定不择手段,也要把他抢过来。第一章 重生第一眼,
我看见妻子藏起来的人重生后第一眼,我看见妻子养在外面的男人。雨下得很大,
砸在车窗上,噼里啪啦,像是要把这几年所有的沉默都砸烂。我坐在车里,
看着路灯在雨幕里晕开一圈圈昏黄的光,视线却不受控制地,落在不远处那把黑色的伞下。
伞很小,只能勉强遮住两个人。女人是我的妻子,苏宛。男人,是她藏了五年的人。上辈子,
我忍了他五年。从结婚第一年发现端倪,到第三年确认事实,
再到第五年那场耗尽我所有力气的车祸,我一直假装不知道。
我假装看不见她手机里暧昧的消息,假装闻不到她身上不属于我的香水味,
假装听不见深夜里她对着电话那头轻声细语的温柔。我是她名义上的丈夫,
是她应付家人的盾牌,是她维持体面的摆设。而他,是她放在心尖上的人。
所有人都夸我脾气好、性格稳、是万里挑一的好丈夫。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所有的温和、所有的包容、所有的不动声色,都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自欺欺人。
因为我欠她。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给不了她一个妻子最想要的东西。我是个同性恋。这件事,
我藏了十七年。从青春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男生心动开始,我就把这份心思死死压在心底。
我不敢告诉父母,不敢告诉朋友,不敢告诉任何人。我按部就班地读书、工作、相亲、结婚,
活成所有人期待的样子。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听话、足够负责、足够体贴,
就能抵消掉我给不了她爱情的亏欠。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在一段无爱无性的婚姻里,
安稳体面地过完一生。直到那场车祸来临,意识消散的最后一秒,我脑子里闪过的,
不是父母,不是苏宛,而是一张清瘦、安静、永远带着一点疏离的侧脸。是他。
是苏宛藏在外面的那个男人。我到死都没问过自己一句——我到底是在忍他,
还是在忍我自己?再次睁眼,世界天翻地覆。我回到了结婚第四年。
回到了我还没有彻底麻木,还没有被那场车祸带走一切的时候。雨还在下。
车窗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我坐在车里,看着那把黑伞下的两个人。苏宛微微仰头,
在跟他说什么,嘴角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温柔笑意。而他,微微垂着眼,安静地听着,
侧脸在雨光里显得格外干净柔和。下一秒,他像是察觉到什么,忽然抬起头。
视线直直穿过雨幕,落在我车上,落在我身上。四目相对的那一瞬,
我浑身的血液像是瞬间凝固,又在下一秒疯狂地冲向头顶。心跳失控,呼吸失控,
连思考都彻底失控。他的眼睛很淡,是浅褐色的,像浸在温水里的琉璃。睫毛很长,
垂下来时,会在眼睑下投出一小片柔和的阴影。皮肤很白,白得近乎透明,
在这样阴沉的雨天里,反而显得格外惹眼。就是这张脸。我忍了五年,躲了五年,
自欺欺人了五年。可这一次,当他真正抬眼看向我的时候,
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清晰到可怕的念头——我终于明白,苏宛为什么会出轨。也终于承认,
我为什么会忍了五年,都舍不得拆穿。因为这个人,太干净了。太安静了。太容易让人,
一眼就栽进去。上辈子,我为了责任,为了亏欠,为了体面,亲手把自己的心封死。
我看着苏宛奔向他,看着自己在这段婚姻里一点点腐烂,
看着那份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心动,烂在心底,发霉发臭。可这一次,我不想再忍了。
不想再装了。不想再为了任何人,委屈我自己一辈子。雨水顺着车窗滑落,模糊了他的脸,
却清晰了我的决心。我坐在车里,指尖紧紧攥着方向盘,指节泛白。
心底那个压抑了两辈子的念头,终于破土而出,疯狂生长。这辈子,我决定不择手段,
也要把他抢过来。第二章 模范夫妻,不过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戏雨落下来的时候,
我正站在落地窗前发呆。这套房子在市中心最高的住宅楼里,一百四十平,装修精致,
视野开阔。这是我和苏宛结婚时一起选的,我当时说,要给她一个最安稳、最敞亮的家。
现在想想,真是讽刺。家再大再亮,也装不下两颗同床异梦的心。客厅没开灯,
只有窗外路灯的光透进来,在地板上铺开一层薄薄的冷白。雨点打在玻璃上,
一道一道往下淌,把对面居民楼的灯光切割成模糊的碎块,像极了我这几年支离破碎的生活。
手机还攥在手里,屏幕亮着,是我妈刚发来的消息:小洲,周末带小宛回来吃饭吧,
你爸念叨你们了。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没有回复。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说我们很好?
说我们恩爱和睦?说我们是所有人羡慕的模范夫妻?每一句,都像一把刀子,扎在我心口上。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微弱的送风声和窗外连绵不断的雨声。我忽然想起来,
这套房子我们住了三年,我从来没觉得它这么空过。空得让人发冷,空得让人窒息。
主卧里永远摆着两张被子,中间隔着一道谁也不会跨过的距离。苏宛睡左边,我睡右边。
每晚互道晚安,语气客气得像合租多年的室友。她是我的妻子。我是她的丈夫。
我们是一场完美的表演。三天前,所有的平静,第一次被撕开一道小口。那天晚上,
苏宛的手机放在餐桌上充电,屏幕忽然亮了一下。我端着水杯路过,视线不经意扫过。
只是一眼,我就看清了那条弹出来的消息。备注很简单,只有一个字母:L。
内容只有两个字:想你了。我端着水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心跳没有加快,
情绪没有波动,甚至连一丝愤怒都没有。只剩下一片死寂的麻木。
我看着那条消息在锁屏上停留了几秒,然后自动消失。就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就像那个人,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婚姻里一样。我喝了一口水,水温刚好,
却冷得我胃里发疼。我把杯子轻轻放回厨房,转身回了书房,像什么都没看见。那天晚上,
苏宛回来得很晚。她进门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很淡、很干净、不属于我的香水味。
我说:回来了。她说:嗯,洗洗睡了。我说:好。她进了浴室,
水声哗哗响了很久。我坐在书房里,盯着电脑屏幕,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结婚四年,
我什么都知道。她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她知道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她需要这段婚姻,应付父母,应付亲戚,应付这个世界对一个未婚女人所有的打量和指点。
我需要这段婚姻,掩盖秘密,扮演正常,完成我作为儿子、作为男人的人生任务。
我们是两只困在笼子里的鸟,各自守着自己的栏杆,互不打扰,相安无事。唯一的区别是,
她的笼子外面,还有一片可以飞去的天空。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天空。或者说,
我以为我没有。直到刚才,站在窗前,看着窗外无边无际的雨,我忽然觉得很累。那种累,
不是身体上的疲惫,是从骨头缝里一点一点渗出来的倦意,像潮水一样慢慢往上漫,
漫过脚踝,漫过膝盖,漫过胸口,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心想,要不就这样吧。就这样过下去,
过一辈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幸福,假装安稳,假装一切都好。反正,也不是不能活。
就在这时,手机又响了。不是我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我皱了皱眉,点开。
是一张照片。照片拍得很糊,明显是偷拍,角度歪斜,光线昏暗。
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画面里的两个人。苏宛侧着脸,笑得温柔又放松,
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模样。她身边站着一个男人,背对着镜头,只露出一截清瘦的后颈,
和半边线条干净的肩膀。就是这截背影,我记了五年。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很久。
雨水在玻璃上不断流淌,把照片里那个人的轮廓冲刷得模糊不清,却又在我心里,
刻得越来越清晰。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一分钟,十分钟,还是半小时。雨没有停,
手机屏幕自动熄灭,又在下一秒亮起。还是那个陌生号码,发来最后一条消息,
带着赤裸裸的恶意和嘲讽:你老婆在外面养男人,你不知道吧?我看着那行字,
忽然轻轻笑了一声。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从结婚第一年就知道。那个男人叫陆延。
二十四岁,比苏宛小三岁。没有稳定的工作,在城西一个旧厂房改造的艺术区里,
帮人看画廊,偶尔卖点自己画的画。苏宛每个月都会往一张他名下的卡里打两万块钱,
用的是一个我从来没在家庭账单里见过的隐秘账户。他住的地方,我去过。他常去的小店,
我知道。他喜欢喝的咖啡,不加糖,只加一点奶。这些事,我都知道,
甚至比苏宛知道得更清楚。可我从来不说。不问,不拆穿,不爆发。不是因为我大度。
不是因为我不在乎。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欠她的。结婚那天晚上,闹洞房的人终于走光。
苏宛穿着一身红色的敬酒服,安静地坐在婚床边,脸颊红红的,不知道是喝酒喝的,
还是紧张。我站在她面前,看着她低垂的眼睫,心里一片酸涩。我想说,对不起。我想说,
我给不了你爱情。我想说,我是个同性恋,我们离婚吧。可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口。话到嘴边,
只剩下沉重的无力。我只是伸出手,轻轻替她摘下了头上那支沉重的发簪。
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头发,她微微一颤。她说:谢谢。我说:早点睡。那天晚上,
我们背对背躺着,一夜无话。我睁着眼睛,看着窗帘缝里透进来的月光,
心里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沈洲,这辈子就这样了。她是个好姑娘,你不能害她。
你给不了她爱,但你可以给她安稳,给她体面,给她一个不会被人指指点点的家。我以为,
这就够了。可我忘了问,她到底想要什么。我忘了问,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后来的事情,
一件一件,如期而至。她开始晚归,开始对着手机偷偷笑,开始在我面前心不在焉。
有一天晚上,她喝了一点酒,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她站在玄关换鞋,忽然抬起头,
看着我,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沈洲,你爱我吗?我愣住了。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里面有期待,有迷茫,有委屈,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没察觉的绝望。我张了张嘴,
却一个字都答不上来。我爱她吗?我感激她,心疼她,亏欠她,可我从来没有爱过她。
那种男女之间的心动、占有、欢喜、嫉妒,我对她,一丝一毫都没有。她看着我沉默的样子,
轻轻摇了摇头,自嘲似的笑了一下:算了,当我没问。她转身上楼,背影单薄又孤单。
我站在楼梯下面,看着她的背影,想开口叫住她,想解释,想道歉,想把所有秘密都说出来。
可我最终,什么都没说。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也再也没有试图解释过什么。我们用一种最沉默、最残忍的方式,达成了永久的默契。
她去找她的心动,我守着我的牢笼。只要这层窗户纸不捅破,
我们就能继续扮演一对恩爱夫妻,继续维持这个看似完整的家。四年了。
我以为我可以这样忍一辈子,演一辈子,自欺欺人一辈子。可此刻,











